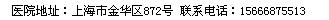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肩部挫伤 > 患病因素 > 14梦与健康
14梦与健康
14、梦与健康
赛斯谈治疗性的梦/赛斯与一个友人在梦中谈话/如何用梦来促进健康
我的一个学生苏·华京斯,心灵禀赋很高,并且相当擅于利用梦。当她寄给我这小笺,连带着一个梦的剧本时,她和她丈夫卡尔住在附近一个城里。那个梦美妙地阐明了梦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联。她幽默地起了个标题:“肩膀简史,或卡莉·纳逊关于坏关节的说法是对的。”
一九六七年,我由大学回家后不久,我第一次注意到,当我抬右肩时,它会痛——后来我才知道是典型的滑囊炎征候。不久之后,症状渐渐减轻。然后一九六八年,症状又回来,而且持续了差不多三个月,才慢慢消失。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又回来了一会儿。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又严重发作了一次,反反复复,一直到十月我儿子出生。自那时开始,症状每况愈下,直到上个月我一直无法将右手插入我牛仔裤的口袋、梳头或做任何事,那会引起我右肩胛骨及右手一直到指尖的剧痛。
瑜伽及“心理时间”暂时令症状减轻,但到上周,僵硬恶化到我整个肩膀痛得象卡住的砂纸一样。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对婴儿大吼,那令我觉得糟透了,然后,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五日,我有了以下的梦:
我来到罗和珍的公寓,碰上了一节赛斯课。我坐在罗旁边,而他一如往常的在作记录。赛斯(身为珍)立刻转向我。他的声音几乎带着怒意,但却并非没有同情心的。“喂,我要告诉你该做什么,”他说,“但我将不对你使用文字的那个部分说话。”
他开始长篇大论,谈处理攻击性及以可接受的方式予以表达的方法。在这时,我批评性的自己与我正接受讲课的“梦我”分开了。(换言之,苏变得觉察到了她自己及作梦的自己。)我批评性的自己马上觉得被排斥,因为它无法了解或转译那讲词。不过,它仿佛有一种明确的作用,也许是与肉体相关的。两个自己都同样地觉察。
赛斯随即坐在我的“梦我”面前,喂它吃某种象壳类早餐食物的东西。我批评性的自己随即变得不高兴起来,几乎觉得那梦是没价值的。然后赛斯对批评性的自己说:“这是象征性的……供思考的食粮……比你知道的复杂得多,并且非你了解的你任何一部分所能了解。”梦自己立刻变得平静了,几乎象被催眠了似的。批评性的自己则一直在想,这不可能在梦里发生。
赛斯又开始讲话,而我批评性的自己开始消失。我问:“赛斯,我有没有一天会了解这个?”答案遗失了,不过我感到在我听不到的讲课里收到的“新知”正在治愈我,而做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则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当我醒来时,我的肩膀、手臂和手都完全轻松自由了。皮下的肿块——我的医生称之为钙肿块——仍在。但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能毫无困难地动我的肩膀。我也能伸进我的裤袋。我面部皮肤有些面皲,连同发作了三周的痉挛,也都消失了。
在结尾时,苏补充说:“当然,梦我只是那起动力。我的内我一直知道该怎么做。或许它只是忘了如何维持一个整齐的档案!”
在此,赛斯有没在梦里对苏讲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一个梦,症状消失了。她曾担心那症状,而向她的内我求助;而那个梦是她的答案。当然,苏的无意识很可能采取了一个权威人物的样子,以使有关攻击性的资料以最大的冲击力传了过来,而用赛斯做为名义上的头头(如果你想要相信赛斯是我无意识的产物,那么你必须承认,对别人无意识的目的他颇有帮助,并且对他们具有一种真实性,与他和我的关系无干。后来的例子将使这一点很清楚)。
赛斯会称苏的梦为一个治疗性的梦,而他用了许多堂课来谈梦与健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在我们研究治疗性的梦之间,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症状。生病有没有明确的理由?照赛斯说,答案是“有”。
谈疾病和行动
(摘自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六四节)
疾病可被视为阻碍性的行动,代表能量的实际阻塞,行动转入对此人格而言并非最有利的管道。能量显得是浓缩的,并且转而向内,影响了整个系统。它们代表分枝;除了从形成人格架构的其他行动的观点来看,否则疾病本身并不必然有害……
实际上可为人格利用的某部分能量,被消耗在维持这阻碍行动或疾病上。那么,很显然,能被用在对人格系统做为一个整体较为有益的行动上的能量便较少了。
按照在疾病背后原始肇因之起动力及强度,情况有种种不同程度的严重性。如果起动力很强大,那么阻碍性的行动会是比较严重的,为了其自己的目的阻塞住巨大的后备能量。它显然变成了人格的心理结构、身体、电性和化学结构的一部分,甚至多少侵犯到梦系统。
(在此赛斯解释了许多人常觉奇怪的事:如果疾病是有害的,而我们也知道,那么为什么健康不佳的状态有时候留连不去?)
有时候,疾病被人格暂时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即为其危险所在。它不仅是象征性地被接受,而我也不是以象征性的说法在说。疾病往往相当真实地为那人格架构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一旦发生了这事,冲突立刻开始发展。“自己”不愿放弃它自己的一部分,既使这部分在作痛或处于不利之境……
(这有严重的涵意。显然,治愈一种疾病最容易的时间,是在它被接受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之前。赛斯在这节里继续解释征候的持续,及我们为何接受的其他更深层的理由。)
首先,疼痛虽令人不快,它却也是由与加速的意识边缘相擦而熟悉自己的一种方法。任何一种升高了的觉受,不论它是否舒服,对意识都有某种程度的刺激性效果。即使当这刺激可能是令人屈辱的不愉快,心理架构的某个部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觉受,而且是个鲜明的觉受。这种对于痛苦的刺激甚至也予接受是意识之本质的一个基本部分,并且是个必要的部分。
甚至从这样一种刺激的一个迅速而自动的排拒或退缩,在其本身,也是意识认识它自己的一个方法。自我或会企图逃避这种经验,但行动本身的基本天性是认识它所有面向的自己。以一种很深的说法,行动并不分辨快意和痛苦的行动。
这些分辨在后来才在发展出的另一个层面出现。但由于人格是由行动组成的,它在其内包含了所有行动的特性。
(赛斯继续描述形形色色的意识对痛苦的刺激反应的方式,最后宣称:在最深的细胞层面,所有的觉受的刺激都即刻地、自动地,并且快乐地被接受,不论其性质为何。在这层面,并不存在着对威胁的体认。“我”的分化尚不够明确到会害怕毁灭。)
在此,行动认知它自己,并且体认到其基本的不可摧毁性。它不怕毁灭,因为它也是新行动将自其中演化出来的毁灭的一部分。
具身体结构的复杂人类人格已演化出一个高度分化的“我”意识,它的特性原本就会企图保持“本份身体”的明显界限。为此之故,它必须在行动之间做选择。
但在这圆熟的完形(gestalt)之下的,是它存在较单纯的基础,而的确包含了对所有刺激的接受,非如此则不可能认清身分。没有这种接受,身体结构绝不能维护住它自己,因为其内的原子和分子经常接受这种刺激,甚至欢喜地忍受它们自己的毁灭。它们在行动内觉察到它们自己的与之分离,以及它们在行动内的实相。
现在你们该了解为何甚至阻碍性的行动也能被人格如实接受为它自己的一部分,以及如果想获得任何进步的话,为何必须要努力怂恿人格去放弃它自己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也被人格的几个特性所助,就在于它是一直在改变的,而其弹性会很有益。我们只不过想改变人格的能量移动的一些方向。人格必须了解,一种阻碍性行动对整个结构来说,是一种困苦,而且自己的这个特定部分对原始人格而言并非必要。接受这阻碍性行动的时间越久,问题便越严重。
(但疾病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呢?照赛斯所说,是可能的。)
人格的整个焦点可能由建设性领域转变为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疾病的地方。在这种情形,疾病往往代表一个新的使之团结的系统。如果人格的旧团结系统损坏了,疾病,被用为一种暂代性的紧急措施,可以维持住人格的完整性,直到一个新的建设性的“团结原则”取代了原来的。
在这种情形,疾病不能被称为一个阻碍性行动,除非在目的已达后它仍滞留不去……即使在那时,你在未知全部事实时,也不能遽下判断,因为疾病仍能给人一种安全感,被留在手边做为随时可用的紧急设备,以防万一新的“团结原则”失效时可用。
“团结原则”是成群的行动,人格在任何特定时候以之为中心而形成。当行动被允许无阻地流动时,这些原则通常相当顺畅地改变。当行动不被允许跟着人格已演化出来的表达模式可管道而表现时,那么便发生了能量的阻塞。
这些必须被理解为,疾病不是与人格分开的什么东西,却是变化中的人格的一部分。它们往往指出内在问题的存在。它们往往有暂时的作用,引导人格离开其他更加严重的麻烦。在此我并不是说疾病是好的。我说的是,疾病是组成任何人格的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它是有目的的,而不能被视为是外来的侵略。
在这特定的一节里,赛斯描述疾病为行动的一部分,但,如他明白指出的,这并不意谓着含有对心理或心灵价值的任何否定。不过,行动的性质是重要的,因为赛斯声明:
人格是同时性的行动;它是由层层相因的行动所组成的。其一部分意识到它觉察自己为行动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试图置身于行动之外,袖手旁观。这个企图形成了自我,而自我本身也是行动。
如果疾病是由外面被扣到行动或人格上,那么个人会是在外在因素的掌控之下,但事实却非如此。人格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但以最基本的说法,它选择那些它会接受的行动。
一个疾病能被拒斥,生病的习惯能被拒斥。当行动被允许自由流动,那就不会发生对行动神经质的拒斥……所有的疾病几乎总是另一个行动未能被贯彻的结果。当被抑制的行动的路线开放了,途径开放了,这种疾病自会消失。不过,那被阻挠的行动也许是个会招致灾祸的行动,却被疾病阻止了。
让我们来想一下苏的症状,照赛斯的说法,那症状是被爆炸性的、被压抑的攻击性引起的。苏自小被教以去压抑情绪,但如今到了非表达不可的时候。她想出手攻击却觉得不应该,而被否定的行动随之压抑住一般而言会出击的右臂的机能。按照赛斯的说法,甚至钙质的沉积也是存积在身体里的受压抑能量的累积。
在她的梦里,苏被给予了资讯,告诉她如何去释放和创造性地利用这能量。虽然她清楚地记得这梦,并且立刻看到其结果,那资讯却没被给予有意识的自己(甚至在梦的戏剧里也没给予),而是给了与身、心机制更密切相关的其他层面。结果手臂和肩膀有了完全的活动力,但仍留下一些由钙质沉积引起的疼痛。
在一九七0年五月十二日,作那个梦的几周之后,苏有了另一个跨越作梦与醒时实相的治疗性经验。她正在看一本谈艾德加.凯西(EdgarCayce)一生的书,她的肩膀便开始痛起来。她突然有个行动,翻查那本书,找到她先前注意到谈及给滑囊炎的肩部瑜伽操的那一段。当她读这一段时,她听见一个声音大声说:“放湿的茶袋上去。”
她吓了一跳,抬起头看。那声音听起来几乎象是来自一个收音机。它又说:“放湿的茶袋上去。”苏写道:
因此我去拿了些茶袋,觉得太可笑了。我奇怪是否该把它们直接放在肩膀上,或垫一块毛巾,而那声音说:“直接的。”我脱掉上衣,躺下来,把茶袋放在肩关节上面。
“低一些。底下才是问题所在。上面只是露出头的。”因此我翻过身,将茶袋移到下面,而突然间,我调准到我脑袋里进行的一个对话。有两个声音,一个比另一个略大声,在讨论这事。
“要放多久?”第二个声音问。
“半小时。”第一个声音回答。
“多少天?”
“每一天。应该只要花六天,但必须更清楚地了解状况。六十天。”
在这时,我开始觉得困了。“放松,”大声的声音说。“放松食指,放松双腿。让血液流通。吸入生命,呼出毒素。”
我打了十分钟瞌睡。当我醒过来时,痛已消失。我一直在做瑜伽操,并用茶袋,而痛没有回来。
两周后,苏在半夜被同样的两个声音吵醒了。“现在情形怎样?”第一个声音问。
“好多了,”第二个声音回。“瑜伽练习在修补影响到肉体系统的效应。她也在学习别将攻击性导引到肩膀上。”
在治疗了六天之后,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钙质肿块也没了。自那时起,在少数几次压力大的时期,苏的肩膀会不舒服,但她学会了,只要重读最初的赛斯梦,立刻会使肩膀再度恢复正常。这些经验是极有价值的,并且产生了不可否认的结果,并且只要苏容许情感能量正常释放和表达,效果都可持续下去。
照赛斯所说,健康不佳主要是破坏性的思考和感受模式引起,它们直接影响身体是由于它们落入的电磁系统内的特定范围。举例来说,并非坏的健康先发生,结果产生不健康的思维,而是其反面。赛斯宣称:
疾病的治疗主要必须藉由改变基本的思考习惯。除非做到了这点,否则毛病会以不同的扮相一而再地发作。不过,身体有能力治疗它自己,而该给它每个机会去这样做。
在大多数情形,(朝向治愈的)刺激来自自己的更深层面,在那儿它们可以被转译成个人潜意识能用的方式。在这种例子里,这些感知可以找到通达自我的途径,以灵感或直觉性思绪的样子出现。
许多这种直觉是在人格离了体时或在梦境里出现……任何思绪的影响是相当精准明确的,并且是由于它本身的电磁性身份之本质而发生作用。肉体运作于某些电磁模式之内,而其他的电磁模式则对肉体发生不利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这些影响改变了细胞的实际分子结构,则由于引力法则,习惯性的模式将会起作用。那么,一个破坏性的思绪不但对有机体的现状有危险,并且就“未来”而言也有危险。
再次的,苏的“声音”是否属于确定的无形体幽灵,或它们是否是治疗性幻象被用来令她的意识心印象深刻,并没什么区别。反正它们给她的指引和教导有用。在近来一次ESP班上,我们正在讨论这事时,赛斯透过来说,他在那个梦插曲里真的和苏沟通过。
赛斯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三日第一九八节里,第一次谈到治疗性的梦——虽然他从一开始就坚称内我有能力治愈身体。在这一节里,他精确地解释了这样一种梦如何在身体系统上发生作用。
我们有一阵子没谈到内在感官了。到如今,你们应该领悟到它们也有一种电磁的实相,而精神性酵素有“点火”的作用,引发内在的反应。在梦境里,这些反应很容易被触发。这是由于降低了自我的防卫结果,因为自我设立了控制,而对“在醒时状态”种种不同的内在管道产生抗拒作用……
在许多例子里,一种破坏性的心态在梦境里一夜之间便被转变成建设性,而整个的电磁平衡已被改变了。在这样一种情形,负离子形成一个电性架构,在其内治愈是可能的。当自己感觉到一种绝望感,而自动打开了通到人格更深层面的管道时,最常发生这种治愈性的梦。
总之,我们发现一个几乎即刻的再生,一个看来仿佛是立即的痊愈,在某一点那有机体几乎奇迹似地开始好转。在比较不惊人的例子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举例来说,一种仅仅是令人烦恼的健康问题突然消失了。
透过自我暗示,经由练习,可以引起这些治疗性的梦。暗示(即是行动)有它自己的电磁效果,已经开始发动了某种治愈过程,而同时也导致了其他过程的形成。
这种内在的治疗可以在形形色色意识的其他层面发生,在那儿它们可能被具有美感或愉悦性质的外在刺激引发。其他的外在情况也有影响。举例来说,参与大团体常常是有益的,不仅因为可将注意力暂时由自己移开,并且也马上可以运用更广大的电磁范围。
个人的整体健康是很重要的,而电磁属性的微妙平衡也一样……当有机体深深地陷入了破坏性的模式,那时在梦境有时会感受到此点,因而破坏性的梦也加进整个情况里去……因此之故,用自我暗示带来建设性的梦是大有裨益的。
赛斯也谈到,梦可以完全反转沮丧的情绪,而这种“改变情绪”的梦,也可以透过利用暗示而制造出来。一个下雨的三月早晨,我决定去遵守他的指示。我发现我已忧郁沮丧了一个多星期——由于我没听到出版社的消息,也由于我在画廊碰到了问题而烦恼。
天空很暗,下过一阵小雨,有暴风雨的预兆。在郁闷地坐在书桌旁一个小时,试图把心放在我的书上之后,我决定小睡一会儿。我走进卧房,钟上显示是十点三十分。我将闹钟设定在十一点,便躺了下来。刚在要入睡之前,我给自己暗示要作一个会提起我的精神,并且恢复我天生热诚的梦。
我躺在那儿,觉察到一种越来越不安的感觉。突然我觉悟到我正听到声音,但它们仿佛是来自我脑袋里。它们稳定地变得越来越大声。我确知我仍醒着。声音涨高了。我觉得好象一架收音机在我头里面调到了最大音量,但电台却混在一起了——因为我听不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反之,我仿佛听到片段的谈话。我真的被吓着了,我摇摇头,并且四下看看。
每件事都是正常的。早晨仍是黑暗而阴沉,透过百叶窗可见外面的灰光。但现在声音真的是震耳了。我拼命试图找到那来源。然后我才发现床头桌上的电晶体收音机正发出很大的响声。我把它关掉了。但我没想到,在现实里,我们家中并没有这种收音机。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那声音仍在持续着!然后我“记起来”在罗的画室里有另一架收音机。声音一定是从那儿来的!我跳下床,快跑到画室。收音机在那儿。我很快地伸手去关它,而受到一次很严重的电击。不仅如此,那声音事实上变得两倍响!
现在我太害怕而不敢再去碰收音机,或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这个收音机事实上也不存在)。反之,我跑过卧房和浴室,跑到起居室里。
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一动也不动。暴风雨已来了。外面是大雨倾盆。里面的每样东西都奇怪的静默着,那声音忽然停止了。整个房间似乎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但等什么呢?完全茫然之下,我看看四周,试图了解我的处境。而这得花些功夫。不可否认的,一扇门取代了我们的中央凸窗。我好奇的走近它,终于将它打开了。
在这儿我发现了一套细致的黑木桌椅,而再过去,是另一间宽敞的公寓。我再度停下来;这公寓打哪儿来的?然后我仿佛觉得,我在某个模糊的过去曾看过它而又忘了。的确,当我急忙走过门廊时,我仿佛还记起其他这种公寓。
门廊开向被用作服装店的一个大的中央区域。他们正在为一次大减价做准备。我想起来了,这些人是那同样被想起来的我过去的一些朋友,而我以前以同样的方式来探访他们。人们看到我,立刻认出我来,而非常欢喜的欢迎我。
当我们闲聊时,我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满足感,并且奇怪我怎么可能忘记我们先前的访晤。随之有一场快乐的谈话。在某一刻我记得我走下一个楼梯,同时一个年轻英俊的黑发男人抓着我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我也注意到一件可爱的绿夹克,而领悟到在我上回来访时,把它留在我朋友处了。
我和朋友提到那些其他的公寓,希望去探查它们。朋友们认为那会很有趣,而提议和我同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探险的感觉。我记不得我什么时候觉得这么好玩过了!然后我想起我必须在午前回家,准备罗的午餐。虽然我很想留下来,我还是离开了我的朋友,答应那天下午再回去。
下一幕,我发现自己在雨中跑出去后院,我把我的香菸包掉在湿地上了,拣起它们后,我惊愕地发现它们根本没湿。而同时我在我衣袋里发现了另一包香菸。这真的令我停了下来。我是如此确定我只有一包菸。当我站在那儿试图弄清楚这件事时,一个报童走过草地来,叫道:“嗨!”
我抬头看他,这次真是搞糊涂了。他明明不是我们现在的报童,却是几年前,在另一个城里送报给我们的报童。他不可能还是同样年纪,而且还在艾尔默拉送报!此外,我们只订了晚报,而现在仍是早上。
我才第一次感到奇怪:这可不可能是场梦呢?我心底涌过一阵失望。如果我是在作梦,那么当我醒来时,这些公寓就会消失了。我再也不能去探险了!我再看看院子。是我们的院子,周遭的环境极为清晰。然后,好象完全没来由地,闪过一种自由和快活的感觉——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去看那些公寓!我是在我身体外面,我的身体在床上。
有了这个了悟,我的感官变得超级警醒了。院子及在我视野内的每样东西都具有重要意义,活生生且超级真实——仿佛比在我一生中任何别的时候都来得真实。在同时,我想起了我在十点三十分躺下,而显然已超过了我给自己的半个小时。不知为什么闹钟没吵醒我。我该回去了。同时呢,我却完全有意识且警醒的在院子里。在那时,我才记起我在躺下前给自己的暗示。我决定立刻回到我的身体。
完全没有过渡阶段地,我在床上跳起来成为坐姿。我立刻查对时钟。由于小按钮按得不够低,所以闹钟没响。无论如何,还没到十一点。实际时间只过了半小时。
虽然当我起来时天还在下雨,可是我觉得棒极了。起先我只记得第二部分的经验,而只在我写这篇东西时,我才记起先前的恐怖插曲。我觉得如此地生龙活虎,以致我对这“梦”的治疗性质毫无疑意。但第一个令人不悦的部分怎么可能是治疗性的呢?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如你将看到的,赛斯在下一节里解释了此点,并且利用这机会对健康和梦做了更多的解释。
直到在本书的后来部分,我才会探讨那次经验的“出体”涵意;反之,在此我想要强调,那“梦”的“改变情绪”的因素,以及它对我的意义何在。在下一节里,赛斯解释这梦,并且显示转世背景、目前问题及个人象征全都被用在梦戏剧里了。那经验有部分是梦。其他则是一种不同的有效的主观事件,而整个作品是应我暗示要一个“改变情绪的”梦而来。
以下是赛斯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第一九九节里说的话:
我很高兴看到鲁柏试了一下谈治疗性的梦的资料。第一个梦的基本行动涉及了他收听到几个声音。虽然他不记得,但它们说了鼓励的话。它们代表了他自己能力的极佳证据,因为它们起初是水晶般清晰而没有扭曲的。总共有四个声音——全是男性。它们属于不再活在物质系统里,但与鲁柏在前生里密切相关的人格。第四个声音是我的。这是个试想建立鲁柏的信心的企图——给他看看,如果他的能力被充分利用的话,他能收听得多清楚。
所以,上面那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梦,却是发生在当他离体时候的经验。它们吓坏了他;因此有当他后来将之变成一个梦时的惊吓感。当他听见那些声音,他没有变得有信心,反而融入一个梦境。他不想接受他觉得他的能力放在他身上的责任,因而在梦里,他在外面找声音的来源,而梦到了收音机那一段。可是,在梦里,“当他关掉收音机后”声音继续下去,因为他知道他是由一个非实质的管道收到它们的。
他又试了一次,在你的书架上,保存我们文稿的地方,发现了另一架收音机。其中的关联很明显,因为他明白赛斯资料和那些声音来自同样的系统。在此他伸手去关收音机而被电到一下。这电击是他的觉悟:如果他关掉他的能力,赛斯资料本身就会停止。与你的关联也很明显,既然涉及了你的房间。如果他能象关掉一架收音机似地关掉他的能力,那么你也会受到损失。
于是,在梦里,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在意识上忘了这部分,以模糊地感到一场电气风暴掩住它。不过,在梦本身里,他发现他的能力就如呼吸一样是他的一部分,而无法随意开关。是有场子电气风暴。他站在屋子中央,被震动的电流触及。虽然他害怕,但却了悟他是风暴的一部分——风暴并非破坏性,却是创造性的,并且特别是实相的一个简单的基本部分。这第二个觉悟使得他能作第二个带有治疗成分的梦。
第二个梦是个扩展的梦。最有意义的层面是那个,在其中许多房间及公寓代表了心灵的发展区域,继续打开的无穷尽可能性,但却是建立在前生经验的可能性。在梦里有转世资料的许多面相,全都加强鲁柏人格的健康成份。
赛斯的诠释在下一节(第二百节)里仍在继续。他说绿夹克代表在一次前生里我有的一个新能力,却被我误用,这新能力现在等着我去领回。那些人全是与我有前生关联的人。这引起了重新发现和喜悦的感受。赛斯说:
当他由栏杆跳下时,是我伸手助他一臂之力。我出现为有橄榄色皮肤的年轻男人。我们全都试图徐徐灌输信心和喜悦,而反应是情感化的。那梦发动了充分的能量以提升鲁柏的心情,并容许他正常的热诚全部回来。将他的坏情绪缩短了几周之久。
梦不只能消除症状(如苏的例子)或完全改变心情(如我的梦),它们还能给我们初期的健康问题的预警——如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在我们灵异经验的早期,有天晚上,我梦见我看到罗站在厨房水槽旁。他弯下腰并倒在地板上。那个梦令我惊吓得很厉害,以致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说:“那个梦吓坏我了。我不想记得它。”换言之,我发现自己正在想要删除那个梦。光是这个就告诉了我它必然是重要的,所以我强迫自己把它立刻写下来。我甚至没告诉罗这个梦。
三天之后,罗走进浴室,突然在浴室洗脸盆边昏过去,跌到地上不省人事。如果我留心了这个梦而告诉了罗,能不能阻止这件事呢?若我告诉了罗,我现在认为,透过梦治疗或在一个轻度出神状态,他可能会发现症状后的理由,而免掉他自己一段痛苦时间。
内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健康状况。有一次,我有一些症状,我便用了暗示、自我分析和梦治疗等组合的治疗方法。我似乎有所改善,但想做个内在的查核。有天晚上,我要求作个会让我知道我进步了多少的梦。
那天晚上,我梦到我在被一位我认识的医生检查。他告诉我,问题差不多解决了。当然,在这个例子里,我显然是用一位权威人物来使我的意识心印象深刻。
并非所有梦到生病的梦都该照单全收。它们往往是你心境的象征性诠释。你可以要求另一个梦以澄清在你第一个梦里的象征。在第一七三节里,赛斯说:
就如人格被任何行动所改变,它也会被它自己的梦改变。正如人格被外在环境塑造,也同样被梦塑造,那梦是人格所创造的,而又有助于人格,形成其内在世界。对全我而言,外在与内在行动之间,鲜少区别。自我才做这种分别。人格的核心并不……正如一个人格藉由对实际情况反应而改变了它,因此他也以同样方式改变他的内在或心灵的情况……
在梦里,你给了那些在正常醒时实相的限制下,无法适当表达的行动的自由。如果人格很能干地处理他的梦活动,那么有问题的行动在梦里便得到了释放。不过,当自我太顽固时,它甚至会试图检查梦……而甚至在作梦情况里,也没全然容许行动的自由。
如果这个解决方法失败了,阻碍性行动随即将以一种身体的疾病或不大好的心理状况具体化。如果一个人有无法在日常生活里表达的强烈的依赖感,他将在梦里表达。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么他可能发展一个容许他在实质生活中表达依赖性的疾病。不过,如果他觉察到有问题,他可以要求释放这感觉的梦。
那个人不一定必须记得这样一个梦。不过,心理上,这样一个经验会是有效的,而依赖性表达了。我再怎么强调此点都不为过:对内我而言,梦经验和任何其他经验一样真实。
于是,藉着利用暗示,种种的问题都能在梦境里解决。我们提过的内在自我(innerego),是这种统合活动的指挥。它是你梦里的“我”,在内我(innerself)之内的位置,就与自我与外在身体的关系差不多。
于是,在适当的暗示下,人格会在梦境解决特定的问题,但如果其解答对(有意识的)自我不清楚的话,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没找到解答。有些情形,自我不只不必要,并且也最好不知道答案。睡着的自己会以自己的方法去听从那些建议。解答也许不以有意识的自己所预期的样子出现。有意识的自己甚至没认知它已被给予一个解答,但它却可以付诸行动……
心理与身体的病,两者都大半可透过梦治疗去避免。相当无害地,攻击性倾向也能在梦境里被给予自由。透过这种治疗法,行动会被给予更大的自发性。在释放攻击性的例子里,所涉及的个人会在梦境内体验此点,而不致伤害任何人。也可以给予暗示,因此他学到透过在梦境里观察自己而了解那攻击性。
这并不象它可能看起来的那样牵强。以这方式,很多乖僻的反社会行为都可以避免。罪案可以被防止。渴望却恐惧的行动不会累积到爆炸性的压力。如果容我耽溺于一个幻想的话,理论上你们可以想象一个梦治疗的大规模实验,由睡眠中而非清醒时的国家来打仗。
(不过,实际做来,)还有许多必须了解的考量。举例来说,如果问题是在攻击性,那么,最初的建议应当包括一项声明,即攻击性并非对某个特定个人而发。潜意识很能以这方式处理状况。这可能看来象是个双重检查,但在所有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攻击性本身,而非作梦者也许决定想发泄攻击性的对象。
当攻击性透过一个梦释放时,并不需要一位受害者。我们不要给一个人建议他在其中攻击另一个人的梦情况。这有好几个理由,包括你们尚不了解的心电感应性的实相,以及不可避免的罪疚模式……
一般而言,我们并不企图以梦行动代替实际行动。在这儿,我们在说的是潜在的危险情况,在其中,一个人显示出无法透过平常的适应方法去应付这些心理行动。没有人能否认,在特定的时候,一个梦中人打的仗会比一场货真价实的仗的伤害要少些——再回到我幻想的奔放上。不过,会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因为,再次的,基本上人格并不分辨睡时与醒时事件。
再次的,如果人格有相当好的平衡,那么他在梦实相里的存在会加强他实质的存在。你是涉足于耍弄两个实相的把戏里。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人格的整个经验,你必须看到它在两个实相内的运作。
治疗白癜风的中成药北京治疗白癜风到哪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