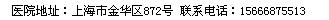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肩部挫伤 > 患病影响 > 王小木逛天堂上
王小木逛天堂上
作者简介:王小木,原名王君,湖北荆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八期学员,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小说月报》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等作品一百多万字。小说多次被各种选刊选载。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香精》《代梅窗前的男人》。
任见文学艺术馆
1
我叫虾子。我们这地方叫虾子的人很多。这称呼来源于我的母亲。我生活在江汉平原,盛产虾子。一到春夏季节,大沟小河里,只要去捞,一捞就会有一箩筐,便宜得什么似的,几毛钱一斤,虾子们一旦不蹦不跳了,就会不要钱,白送给贩子们。贩子们再拿去贱卖给餐馆里或者熟食店里,用尖椒桂皮八角花椒等等红烧一番,上面撒点紫苏或者香葱,红艳艳香喷喷绿荫荫火辣辣的,摆在玻璃柜里面,当红闷大虾卖。
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小贩,她清早就会挑着篮子,在河边找打鱼的人家进些小鱼小虾,挑到镇上,坐九路车,到城里的菜市场里去卖。傍晚的时候,她坐九路车又回来了,挑着两只竹篮子,篮子里面放一些长着虫眼的苹果或梨子、蔬菜,带着满身酱油颜色的疲惫。只要我找她要钱要吃的时候,她就有气无力地说,你就是一只虾子呵!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至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我母亲干吗这么叫我。我只知道我的父亲让我的母亲很不如意,他常常到镇上的茶馆去喝茶打牌什么的,回来后他们常常打架。后来,我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们才不打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打了。他们感觉有点老了。我常常跟在母亲的后面,头发乱糟糟,脸上像破了几个眼的画报,脏兮兮的,什么也不说,只是哼哼,哼的目地就是要钱,要钱买糖,要钱买书,要钱交学杂费。母亲就恨恨地掏出钱来,诅咒般地赐给了我这个名字。于是,很多人都跟着叫我这个名字了,后来,这个名字就取代了我原来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是什么?我不认真想是想不起来的。当公安局的人要我把身份证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问我,这是你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低下了头。对于不太明了的事,我都这样对付。他们无法。只好自己对自己说,不错,是她!
我长大了,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想离开这个地方。日夜都想,做梦也想。靠我读书是不可能的,不说我的母亲没钱供我读,就是她有钱供我读,我也读不下去了。我常常把8字写成像我母亲系箩筐的绳子。我还把一道数学题改了三百多遍,但还是没有改对,数学老师当场气得都吐出了白沫了,像我家的水牛倒刍时吐出的白沫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盛产水稻,农忙的时候,女人们都得在水田里插秧。插秧并不像电视和电影里放得那么浪漫好玩,也不像画报中画的那般花红柳绿的漂亮好看。插秧很累很累,要成天弯着腰。累倒不说。水田里不仅长蚂蟥,而且还长水蛇。蚂蟥会顺着人的大腿向上爬,爬着爬着,就爬到腰上去了,有的还会爬到人的腿中间去,只要不被发现,喝饱了血,会藏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变成牛驼精的,牛驼精比蚂蟥更厉害,它会顺着人的毛孔,钻到人的身体里面去,在哪里产卵,生下它们的小毛毛的。当然,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大多都会被人发现的,因为蚂蟥粑在人的身体上,会有一种痒痒疼疼的感觉,用手一拍,它就掉到水里的。水蛇更叫人可怕。它们常常藏在田埂角落里或者草丛里,水一响,它就会冷不丁地游出来,吓得人半死。当然它自己也会吓得半死。它们的背脊由两种颜色组成,白色和土黄色。在水田里,如果不动的话,你就分不清它是何方来的神仙。如果你踩到它们了,它们也会咬人的,咬得人腿杆子血糊汤流的。当然,水蛇没有多大的毒性,是咬不死人,血流一流就没事了,否则的话,我们这里人大多都死光了。
我们村里的女孩大多都出去了。我也想跟她们一样,我不想就这样白白的喂蚂蟥和蛇。可我找不到路,我该怎么样才能出去?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些女孩们都光光亮亮地回来了,她们一个个都变得漂亮多了。我也过去看她们。可她们很少跟我说话。我鼓着勇气跟她们说,我也想出去干活。她们大多都笑了。笑完后问我,你想出去干什么呀?我回答不了。我想像不出来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她们都干了些什么。可我知道我什么都能干的。我有的是力气。我比她们都长得结实,我还比她们都老实。
没有人肯帮我。也没人愿意带我走。在我二十岁的那年,我只好结婚了。对象是别人介绍的,是父亲的一个玩伴介绍的,比我大六岁。母亲说,大六岁的男人应该懂得疼女人的。我当时不懂母亲的话,但后来我还是懂了。等我懂了的时候,才明白母亲的话并不一定是对的。男人大不大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男人的心好不好。等我懂到这些的时候,一切都有点迟了。
2
我的男人叫文华兵,长得还很周正,皮肤也比我白,眼睛也比我大,只是眼睛里面没有东西,很空,叫人看了一眼就不去想这个人了。他是五八村的人,离我们村有十五里路程。村里的人都说我找了一个好看的女婿,于是,我也觉得他好看。觉得好看就是爱情吧?我心里开始甜甜的。结婚后,文学兵的父母就把我分开单过了,他们在我们的屋后另盖了一幢小房子,还说借了许多钱。他还有个弟弟在读高中,他们要管他呢。我很快就怀上了孩子,害口害得厉害。一天到晚嗷嗷地吐。那时节正是农忙的季节,我还得下田插秧,有时候我还要犁地、耙田,因为文学兵常常不在家,他在田里混两下就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能让田里荒着吧?不能。这是种田人最耻辱的事,春种一粒种,夏收一斗粮,节气一错过去,什么都种不成了。我只好一边嗷嗷地吐着,一边牵着牛,扶起犁,耕起了地。有时候,文学兵的父母看不过眼,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什么也不说。等文华兵回来后,我问他到哪儿去了?他也什么都不说,只咳。剧烈地咳嗽。我又累又困,就睡过去了。等孩子生下来后,我才慢慢发现文华兵跟我父亲一样,也是一个跑场子(赌博)的人。因为他常常夜不归宿以外,放在家里的钱也常常不翼而飞。我问他,他就是不说。有一次,我聪明了一次,抱着孩子跟上了他,我发现他上了镇上的楚香香饭馆的二楼。我从小就知道,楚香香饭馆的二楼就是一个暗场子,里面乌烟幛气的,什么都有。麻将,牌九,押金花等等。我小的时候跟我母亲去过。我母亲拖着我,站在麻将桌边呆呆地看着我的父亲把大把大把的钱数给别人。我母亲说,给点我吧,我要买种子。父亲说,滚!母亲又说,孩子也要发目了,要报名呢。父亲说,发什么目?读个屁的书!读了书还不是回来搓泥巴。母亲说,跟家里留点钱吧,缸里没听得米了。父亲举起了拳头,遇上你这个扫帚星,老子不输才怪!你到底滚还是不滚?母亲只好牵着我走了。母亲高一脚低一脚出来,眼睛一黑,竟然从二楼滚到了一楼。父亲的咒语还真灵。听到外面唏里哗啦地响,我看到楚香饭馆的老板娘伸出白白胖胖的脸,朝我们看了一眼后,就缩回去了。
我终于知道,命也会遗传的。
我抱着孩子离开了镇子。我是走回家的。孩子兴许是饿了,开始哭了,我就掐他的屁股,我把他的屁股掐青了。孩子哭得上气接不着下气,哭了一会,又睡着了。我坐在小桥边,看到他青紫的屁股,又开始掐我自己,我把自己的胳膊也掐肿了。
路上有些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四邻八乡的人。有些是摩托车,驮着女人和孩子,那些人笑得很开心。还有些是板车,上面拉着煤或者冬瓜什么的,一遇到上坡的时候,赶车的人大声地吆喝牛或者马,一骂,那牛或者马就把身子弓得紧紧的,像人拉纤那样。偶尔也会过来几辆小骄车,它们只是把一阵灰扬得满天都是,然后就无影无踪了。
孩子睡着了,像石磙一样重。我坐在小桥上,看乌鸦越飞越低,看一个个村子里的灯光在眨眼睛,越眨越眨多,越眨越热闹。看到天黑才回家。
深夜,文华兵才回来。看样子,肯定是血本无归了。我坐在床沿上,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他。他也坐在椅子上,不吭声,偶尔看我一眼。不一会,他又开始咳了起来。咳着咳着,就咳出了东西,是血。他先是吐了一口在地上,然后他抓起桌上的卫生纸揩了一下嘴,血在灯下黑乎乎的。医院检查一下吧。
第二天,医院。医生说他的肺节核已经到了晚期,需要住院治疗。医生还说,这不是癌症,能治好的。
我找他的父母借了两千块,还差三千,我只好找母亲了。我知道母亲肯定攒了钱,她贩了这么多年的小鱼小虾,一定会有私房钱的。母亲借了我三千。母亲说,这是我的棺材本啊,虾子!
文华兵住院了,住了几天后,他就不吐血了,脸色也好了很多。我回家看孩子。医院的时候,文华兵就不见。医生说,他坚决要出院,剩余的钱他也拿走了。我到楚香香饭店去找他。没有他。有个人告诉我,他可能跟着到船上去了,今天有场子开课。
我知道开课的意思,文华兵住院时曾跟我说过。开课就是流动的赌博场所,有的在船上,有的在车上,还有的在荒山野外坟墓边。场子外围有几层暗哨,公安的人来了,放哨的就放出信号,庄家就把所有的人转移了。据说,庄家和暗哨都带着枪的,都是提着脑袋在玩的主。
我不知道在哪条船上开课,没地方去找。在镇上发了一个小时的呆,只好回家了。
三天后,文华兵回来了,脸色惨白惨白的。他躺在床,差不多要哭了。他对我说,虾子,我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呀?我本来想赢的。
我想杀他,但我没有杀他。晚上,他又开始咯血了。我们已经没钱了,还借了许多钱。他休息了一上午,还是咯个不停。我只好又找邻居家借了五百块钱,我骗邻居说孩子得了病,卖了麦子就会有钱还的。
我又医院,我们一前一后离得远远的。医院,医生不让他住院了,医生说钱太少了,只够开一个疗程的药钱。我们只好开了药,回去了。
第二天,我要到邻村还亲戚的帮工。农忙的时候,别人帮过我的,我就得帮别人。孩子放在后屋奶奶那儿。
傍晚,我才回家。
文华兵和另外两个男人在堂屋里打扑克,遍地都是烟蒂和带血丝的痰。文华兵的面前什么也没有,那两个男人的面前都堆着钱,有一个还放着文华兵的药。我问文华兵这是什么意思。文华兵说他的三叔也咯血,拿回去可以卖给他三叔。
我眼睛黑了一下,就把桌子抽翻了。我还在门角里找了把铁锹,逢人就砍。两个男人抓了钱和药跑了,但文华兵却跟我打起来了。他趁我不备,夺下了铁锹,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他这时的力气可真大!我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连哭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被他在地上打得皮开肉绽,全身沾满了泥土和沙子,后来还沾染了血迹。
有个过路的乡邻看到了,过来把文华兵拉开了。文华兵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两脚后,才余怒未消地走开了。
他打累了,就躺在床上咯去了。我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爬了起来。我用井水把眼睛洗了洗,到后屋抱孩子。他奶奶惊慌地问这是怎么哪。我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我抱着孩子走了十五里石子路,回了娘家。我全身疼得火烧火燎的,但我走得飞快。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回去了。我在心里狠狠在咒诅文华兵:让他死吧!去死吧!
我在娘家住了半个月后,伤口渐渐好起来了。文华兵的一个叔伯兄弟来接我了,他说,嫂子,回去吧。华兵哥快不行了!他想看看娃儿。
我回去的时候,文华兵已经被人从床上抬到堂屋里,放在地下了,地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一床被子,他就躺在被子上,闭着眼睛。他的脸严重变形了,白得像石灰。屋子里有股霉腥味。我们这里快死的人都是要躺在地上。据说,躺在地上的人,灵魂就会跑得快。
见他这样,我一点泪水也没有。一瞬间,我觉得他陌生极了,我都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他睁开了眼睛,好像认出了我们,向我们伸出了手。我紧紧地抱着孩子,把头捂在孩子的胸前。我不敢看他。我也不想让他沾上孩子的手。
他母亲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他姑妈曾来看过他,也给了钱叫他去看病的,结果他拿着钱还是去打牌了,打了几天几夜,就被人送回来了,就成了这个样子。
到了晚上十点多,文华兵就走了。我没有哭,我想是应该哭的,但我哭不出来。没有人哭他。不过,断气的那阵,他母亲还是嚎了几声,但很快被她侄女拉走了,他母亲就再也没哭过了。早早就请来的装殓先生跟文华兵换了衣服,把他放进了白板棺材里。棺材是上午刚打的,疙疙瘩瘩的,有些刨叶还挂在上面,还有一股木香。
办完了文华兵的丧事,婆婆就对我说,虾子,孩子我跟你拉扯吧。
我知道她的意思了。儿子死了,这儿没什么事了,房子要还给她了。她们还有个小儿子呢。
我说,好吧。
3
我收拾了我的行李,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感觉有点兴奋,这事好像早就安排好了。我终于要进城了,我什么也不用害怕了。我除了到城里去,我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娘家已经早没有我的位置了,母亲已经有了她自己的打算,已经攒足了棺材本了,对我可有可无。父亲更是活一天算两个半天。他们都活得唉声叹气的。我能到哪里去呢?只好到城里去了。城里的人多,可以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城里还有许多活法。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到了镇里,上了九路车。九路车上有几个鱼贩子,有男的和女的都有。司机找他们打了货票,他们就把鱼担子放在过道里,很多人上车只好从鱼担子上面爬过去。那些鱼虾都还新鲜,看起来很漂亮,还在篓子里跳来跳去,不一会,就不跳了,就死掉了。我怕碰到母亲,就坐到最后面,把头埋得低低的。还好,母亲没来。她年龄大了,有时候腰疼,有时候腿疼。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早晨,路上人少,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有的站台停都不停,我感觉自己像个汽球,在胡乱飘着。我有点晕车,就把眼睛闭上了。
到了城里,转悠了几天,没找到满意的事,只看到饭馆门口有很多要洗碗工的招牌,但里面都是人,吃饭的,送菜的,搬煤的,来来往往的都是人。我很害怕。我不敢进去,进去又不知道该找谁。有天下午,我到人民路上转悠,看到一家板鸭店招杂工,店里面没人,只有一个看起来比我小的男孩守着店门,男孩围着一个围裙,方脸虎脑很和气的样子。我就进去了。我说,我是,我想……。我望了望牌子,脸有点发热,说不出囫囵话。卖板鸭的男孩笑了,明白了我的意思,要我进去找老板娘。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围着皮围裙,在灶台上把一大桶酱酱乎乎的东西往锅里倒,锅里装着鸭,满满的一锅,大约五六十只。炉子里的炉火旺旺的,屋子里热烘烘的,地上湿漉漉的。
见我说找老板娘,她停了手里的活,问我多大了,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我二十三岁。家里没什么人了。
哦——,这么年青就没什么人了?
我低着头,没做声。我觉得没什么好说出口的。
她就不问了,然后说,到这里做是要吃苦的,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洗鸭子,洗内脏,剁鸭子,升炉子,打扫卫生,六百块一个月,包吃包住。如果行,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我觉得还可以,更主要的是,那老板娘还可以,慈眉善目的,一定不会很坏。
这时,锅里的汤滚起来了,香气像饿极的蚊子一样迎面扑来,也让很多闻到的人像蚊子一样扑了过来。那些鸭子在悄悄改变颜色,从肉白色慢慢变深,变成酱黄色,上面有了油腻腻的光泽。
老板娘安排我住在街背面的绿峰小区里。三居室的房子,两套。秋秋也住在这儿。秋秋是她娘家侄子。这是老板娘刚买的房子,跟两个儿子买的,一个一套。一个儿子还在读大学,一个还在读高中,房子还没有装修,只装了几扇门,有时候,老板娘也住在这。一多半时候,她都回家去住,她的家也离得不远,是买地修得两层楼的房子。更多的时候,是我跟秋秋一个住一套。秋秋很喜欢唱歌。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太多情,悲泣到天明……。无所谓,我无所谓,放过了自已才能高飞……。一双筷子耶易呀折断,十双筷子耶抱呀抱成团,抱成团……。高不上去的时候,听起来就像狼嗥。不过,有时候也挺好听的,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就到店里去了,秋秋还可以睡两个小时,但他有时候也爬起来帮忙。只要他起来,就会唱歌,唱得上下楼房都听得见。有人找他提意见,他就说,不唱了,下次不唱了。吵醒你家了!可是,下次他还是唱。想起来,就捂住嘴,想不起来,就唱着下楼了。
六点钟,守夜的老头走了,老板娘就已经来了,她骑上三轮车到屠宰场去进鸭子,我就开始收拾锅灶和炉子。等收拾得差不多了,老板娘把鸭子也进回来了。满满一车鸭子,三百多只呢,上面还有些毛和沥青,我要把它们一个都洗干拨净了,再剁掉鸭爪和脖子,交给老板娘卤。做完这些后,就得洗那些鸭内脏。那些鸭旽鸭肠子鸭蛋们,泡在水里白绒绒黄橙橙臭熏熏的,能逗来一群一群的绿头苍蝇。我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很快就会回来,围在我的周围嗡嗡乱叫,就像来了一片黑云。就这些事,我每天要忙到晚上八点多钟,老板娘比我更累,她还要操心几个人吃饭,还要管记帐,还要管卤鸭子的作料配方,那配方都是保密的,都是她一个人悄悄配好了,混在一起再倒在锅里的,谁也不知道哪是些什么玩意。总之,什么事她都要管,店内店外的,比我累多了。看她那样,我再怎么累,也无话好说。
一天下午,早过了卤鸭子的时间,再不开锅,下午就没有卖的了。老板娘还是没来。打老板娘的手机也没打通,
我到前面店铺里问秋秋,秋秋正挥着大砍刀跟顾客跺鸭子,旁边的女收银员正忙着收钱找钱。收银员是税务局的一个熟人介绍来的,家就住附近,忙得时辰就过来,闲得时辰就回家去,胸前常常湿漉漉的。老板娘说她刚生完孩子,要喂奶呢。
秋秋边哚鸭子边对我说,先到小区去找找吧。
我只好到绿峰塔小区去找了,还没到门口,就听到屋子里有激烈的吵闹声。一个男的跟老板娘在吵。老板娘嘶声力竭地说,你这只白眼狼!你还要我怎么样?你吃喝嫖赌我都可以不管,你还回来离婚?你还有没有良心呵你?
男的说,你看你这个糟样子,哪个男人愿意跟你?
我这个样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你去!你把哪个小B婆娘引来比比,看她强到哪里去,你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要杀了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牲畜!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疯婆娘!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推门进去了。我看到老板娘操了一把水果刀正向男人冲过去,男人已经抓起了一把竹椅子,准备抵挡。见了我,他们都愣住了。我也愣住了。那男人我从来没见过,跟老板娘差不多年龄,眼睛下面长着一对大眼袋。
我低下头,说,我来找老板娘。店里有事。
老板娘把水果刀放在桌子上,把衣服掀起来擦了一下眼角上的泪痕,跟着我走了。
4
老板娘说,他们都出生在农村,一个村里的。刚结婚的那阵,很穷很穷,穷得连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后来他们就到省城去做苦力。他们租住房的房东老汉有一手卤鸭子鸭颈鸭爪的绝活,他有空的时候就卤出一筲箕叫他姑娘拿到巷口去卖,总是一抢而空。老板娘动了心思,想把这手艺学到手。如果学到了,这就是一门生财之道呵!但老汉不想发财,有钱用就行了,也不想让手艺传出去。但常言道:只要主意真,铁棒磨成绣花针,一年半后,老汉还是把绝活告诉了她。老板娘学到了手艺后,就带着家小离开了省城,找了这个地级城市开起了卤鸭店。生意一直不错,十几年过后,他们也挣下了一笔不小的家业,有钱了,她丈夫就变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不管店里的事,把所有的事都甩给了她一个人,只是回来拿钱,常住在宾馆里,离婚的事也经常提,但她从来没同意过。只要拿到了钱,他也没真心闹过。
我说,既然他要离,就跟他离吧。反正有他无他不是一样吗?
老板娘说,离了,家产他会分走一半,就会给一个我认都不认识的婊子!一想到这,我就受不了。再说,孩子们怎么办?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得给孩子们留个好名声呵!
我扶住老板娘的肩膀,把桌上的手纸递给她。
我还看到老板娘把许多眼泪都滴在汤锅里了,鸭子在老板娘的泪水中改变颜色,变成让人吃掉的颜色。
秋秋一整天都没有唱歌。
过了两天,老板娘的男人竟然来到了店里,还在后厨间要跟我帮忙剁鸭子。我站起身望老板娘的脸色。老板娘冲我眨着眼,笑着说,虾子,你让他剁,他剁得要比你快呢。你来加煤,再把卤好的鸭子搬到前面去。
我解下了皮围裙,递给了他。我发现他盯着我胸部看了一会,接围裙的时候,还把手肋在那儿摩蹭了一下。我的脸蓦地红了。我的衣服穿得太少了,上身只穿了一件小背心。这是我在地摊上刚买的,三十块钱,翠绿色的,中间有白色的条纹。早上出门的时候,想着天天都套着皮围裙,里面再穿什么都无所谓的。
我手脚慌乱地把鸭子端到了前店里,在哪儿坐了一会,才回到了厨房里。坐的时候,秋秋也偷偷瞄我的胸部。瞄的时候,他险些被砍刀剁掉了食指。
老板娘在酱鸭子的浓雾中露着笑脸,汗水哗哗地淌进了锅里,滴在鸭子的身上。我看见鸭子在老板娘的汗水中改变颜色,变成让人吃掉的颜色。
一连几天,老板娘的丈夫都呆在店里帮忙。只是有时候早点,有时候晚点。大多数的时间是帮着我剁鸭子。嗵嗵嗵,鸭子飞上飞下,像下雨一样。老板娘对我说,最开始的时候什么事都是我们两个人做,早上三点就要起床,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忙完。那时候,他什么活都抢着干呢,还晓得心疼人,再忙再累也不觉得苦,相反还觉得甜。真没想到,男人有钱就变坏,还不如没钱呢。
隔壁剁鸭子的男人吼道:你哪里来得这么多废话?
老板娘就不吱声了。男人放下了砍刀,出去抽烟去了。
老板娘悄悄对我说,虾子,只要你留得住他,我跟你涨工资。
我留他?
是的。你没发现他看你的眼神?
眼神?
直勾勾的。你看,就像这只鸭子的眼。老板娘用捞箕把一只鸭子从锅里勾了出来,指着鸭子的眼睛说。鸭子刚下锅,身子白白的,眼睛黑黑的,其他的鸭子的眼睛都是闭着的,唯独老板娘捞箕上的鸭子眼睛是睁开的,白的多,黑得少,好像活的。
我走开了。老板娘在我的身后说,虾子,你年青!跟他睡吧,我不会亏待你的。不过,你们发生了什么都要跟我说,不能瞒我。
5
这事儿很简单。晚上,老板娘的丈夫就来了,他是拿着钥匙开门进来的。他们是商量好了,还是他擅自作主来的?我没有问。
他进来之前,我靠在床上,正在思考老板娘的建议,到底跟不跟她男人睡。
他好像还特意换了件红T恤,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眼袋也小了许多。
他一进来就坐在我的床上,摸我的手,夸我的皮肤很好,然后又摸我的乳房,夸我的乳房很好。我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就说,我一点也不漂亮。
他说,漂亮?什么是漂亮?我们这个年龄了,只要舒服就是漂亮。
他把鞋子蹭掉了,先蹭得是左脚,然后是右脚。
跟文华兵一样,我一点也不舒服,刚刚有一点舒服的感觉,他就喊,我完了!他的喊声很特殊很短促,还很恐怖,像被人插了一刀子一样。喘过粗气后,他说,我真的是老了!年青的时候可以四十分钟的。
我问,年青的时候是跟老板娘吗?
是的。
为什么现在又不跟她了?
他不说话了,下地,抽了根烟就走了。
他走后二十分钟,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老板娘开始问我。我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老板娘兴奋地拉住我,说,他真的说我们年青时有四十分钟?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舍不得电灯费,伢们一睡,他就关了灯,催我也睡下。他隔天就要干那事。干得我都烦他了。他求我,说,干完了,才睡得香。呃,虾子,下次,你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不跟我了,是不是嫌我老了?
老板娘又骑着三轮车出去了。这时,街灯刚熄,天还是蒙蒙亮,一些赶早的人急匆匆的,把自行车踏得吱呀吱呀叫,路上的行人很稀疏,空气也很干净。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觉得她的头发很乱,还很脏,短短的,张牙舞爪的,把它们梳梳、理理,可能会顺眼一些。我摸了摸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可能也很乱。我要找面镜子看看。我到处找镜子,第一次发现我们这里是没有镜子的,连一点发亮的东西都没有。我只好把砍刀擦亮了,对着砍刀照了照。我用水把头发理好了,梳成了一条辫子,找了根屠宰场扎鸭子脚的橡皮筋把头发扎好了,开始收拾煤灰和垃圾。
老板娘满头大汗地回来,歇了一会后,就从兜里掏出二百块钱,递给我,说是让我买身衣服,还说顺带买瓶蜂王浆口服液,很便宜的那种,十几块钱。见我盯着她看。她说,傻丫头!完了后让他喝呀,这样身子就不会虚的。
下午,我请假到街上去,老板娘说,去吧!早去早回。
我跟自己买了条蓝色的裙子,化掉九十。到药铺买了一盒野山牌蜂王浆,化掉十八块伍毛,还剩九十多块。我交给老板娘,老板娘赏给了我。
晚上,我穿着新裙子,等着他来。但他没有来。第三天,他才来了。他还给我带了一个银手镯。他说,姑娘伢带银手镯好看呢。
我说,我还是姑娘伢吗?
怎么不是?二十多岁当然是。说完,他又蹬掉了鞋子。
这次跟上次有所不同,虽然时间差不多,但我的感觉有了变化。我感觉身体有股东西在奔跑,它们要出来,但又没有出来,它们堵在了某一个部位。那是一股什么样的东西呢?让我的每根汗毛都很轻盈很柔软,而又很肿涨。
我给他喝了蜂王浆后,就问他,为什么不跟老板娘了呢?她人那么好!
他说,我们不提她好吗?
说说吧。反正也无所谓。
我们已经这样了,跟你说说也无妨。她是个非常小气的人!我亲妹妹的小孩得了急性贫血,找我们借钱,我们的钱全部都在她手里,她却一分钱没借。她不仅不借,还发了一通牢骚,说原来没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躲得远远的,看都不看一眼。现在有了点钱,大事小事都找来了。妹妹忍气吞声地走了。小孩因为治疗不及时,就死掉了。你说,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没有呢。
他说完这个,就不吭声了,默默地抽烟。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抽完了烟,沉默了两分钟,他就走了。我第一次觉得他有点可怜。我也有点可怜。我发现自己有点想他了。一想他,那股东西又回来了,我摸遍了所有的部位,但没有找到。我开始焦虑,把衣服都脱掉了,裸睡在床上。还是睡不着。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啊,他又回来了?一定是他!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身体,这也许就是书上所说的心灵感应。
我像喝了蜂王浆的虫子,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好日子!
赞赏
人赞赏